中國國家藝術網訊:2017年4月28日,第二屆栗山詩會暨百年中國新詩的本土性研討會在湖南湘陰召開。栗山是湘籍著名詩人、評論家周瑟瑟的胞衣地,自去年在栗山舉行過周瑟瑟詩集《栗山》朗誦與座談會后,決定每年春天舉辦一次栗山詩會。本次活動同時是湖南省詩歌學會第31期詩歌沙龍。參加詩會的詩人有周瑟瑟、梁爾源、羅鹿鳴、譚克修、路云、黃明祥、雷武鈴、李不嫁、夢天嵐、陳惠芳、肖歌、吳茂盛、趙海洋、湯紅輝、周春泉、徐漢洲、幽林石子、楊自章、周偉文、馬遲遲、何青峻、李岡、張靈均、葉菊如、朱開見,以及湖南省作協副主席、岳陽市作協主席、岳陽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彭東明、湖南理工學院文學院院長、評論家楊厚均、湘陰縣副縣長湯靜、湘陰縣政協副主席、縣文聯主席熊國庭,湖南本地文藝界代表、朗誦藝術家50多人。活動由湖南省詩歌學會、岳陽市詩歌學會、湘陰縣文聯、中國詩人田野調查小組、《卡丘》詩刊主辦,由湘陰佰嘉麗景酒店、湖南南泉文創公司承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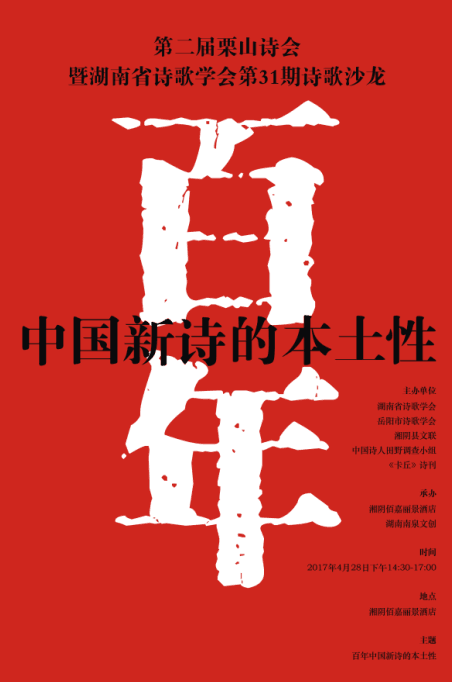
上午詩人們在栗山邊的左宗棠故居柳莊、陽雀湖辣椒產業園參加了第二屆樟樹港辣椒文化旅游節、辣椒與鄉愁詩歌朗誦,詩人們在樟樹鎮辣椒、樟樹鎮本地特色時令蔬菜韭菜、黃瓜、土豆、莧菜中感受到了土地帶給人的愛,品嘗了樟樹鎮辣椒、芝麻豆子茶、土甜酒、紅薯粉等。下午第二屆栗山詩會開始,周瑟瑟主持了詩會。大家就“百年中國新詩的本土性”展開研討。
周瑟瑟說:栗山是我的胞衣地,在我的故鄉舉辦“第二屆栗山詩會”與研討“百年中國新詩的本土性”,對于我個人而言具有特別的意義。我的寫作當然是從故鄉出發,在外轉了一大圈又回到故鄉,這甚至是大多數人精神漫游的普遍路徑。今年恰縫新詩百年,我們討論“百年新詩”不可不談其“本土性”。我與《卡丘》詩刊的同仁們近年在做“中國詩人田野調查”,我們關注的是鄉村重建與傳統向現代轉型過程中人的變化,我還提出了元詩、方言與啟蒙寫作。栗山做為一個詩歌方言成了我的元詩的重要部分,我從栗山的寫作中找到了“語言的本土性”,我的詩歌語言與我的日常生活構成了內在的呼應,我不寫與自身的語言體驗無關的詩。語言決定了你的寫作能深入到什么層次,能解決你與詩之間的什么關系。近年我的詩越來越笨拙、簡樸與口語化,我通過一個人的日常生活發現詩的奧秘,詩的精神困境因為語言的放松與敞開而得到解決,我在大量文本寫作基礎上正在試圖建立“精神的本土性”,我的詩集《栗山》是本土性的,但更是現代性的。新詩百年在全球化語境下的本土性是詩歌文本呈現的具體成色,而不是一個寫作的困境。

梁爾源從“詩歌本土的植根性與狹隘”的角度談了自已的觀點,他認為,本土是詩產生的原始根基和先天養份。如果一個人的詩不能顯示其個性和特點,其重要原因是在很大程度上,詩歌本土的先天基因的變異和養份的缺失。因為一個詩人的原始創作激情,一般都來源于植根在本土的初始的、純凈的、真摯的沖動。這種源自本土的創作火花,構成這個詩人的基本審美取向,夯實著這個詩人向三維伸展的基礎。但本土性的堅守,容易讓詩歌不自主地陷入一種狹隘的美學局限,過分地強調本土性,會讓現代詩歌趨同民歌的創作思維。詩歌的本土性,還體現在創作上對開放性的排斥。體現在傳播和受眾上,容易囿于區域性。因此,詩歌一方面不能擺脫植根的本土性,另一方面又必須堅定打破本土的藩籬,兼容并蓄大千世界的創作養份。
譚克修認為:我們現在越來越頻繁地談論詩歌本土性問題,因為它確實是當代漢語詩歌頭號問題。本土性問題不解決,漢語新詩的合法性就會存疑。談論本土性問題,繞不開本土性與現代性的關系問題。新詩百年以來的路程,可視為是被現代性一路追趕的一百年。總體而言,從五四知識分子詩人,到朦朧詩人,他們的工作主要是把西方的現代性納入漢語傳統。在部分第三代詩人,以及后來者,如部分地方主義詩人,受全球一體化壓迫和對詩歌意識的成熟,對本土性的思考加大了力度,一邊在持續把漢語詩歌進行現代性改造,同時將本土性作為現代詩歌意識之重要一極。若說我們之前對本土性和現代性有過這樣的追問:先有現代性,再有本土性?還是應該先有本土性,再有現代性?這問題其實很難厘清,也沒那個必要。我們需要的是同時解決兩個問題。
羅鹿鳴認為:我們內生的詩性是與生俱來的,他在每一個黃皮膚黑眼睛的人的細胞里。因某種外部引力誘發出來,便寫出了詩,寫得多寫得好便成了詩人!因此,中國人的詩與外國人的詩一樣,天生就具有其本土性。而另一個誘發詩歌本土性的源頭,便是其文化基因與生存環境。從小耳濡目染的中華文明,成了詩歌或隱性或顯性的符號,而環境的影響與詩歌如影隨形。所以說,任何詩人的作品,其本土性是天生的。不管表述的形式如何變化,語言的結構如何創新,使用的是何種語言,只要通過披沙淘金,最后都能找到其本土性的原形。
黃明祥認為,席勒、克萊爾、于堅……他們幾乎都說到,藝術要回到本源。他們集中說的,是要回到催生人類藝術的源頭去,比如詩歌,要回到人類從原始的聲音中分創出文字的初始感受,找到初始的命名路徑,比如音樂,要回到最初的自然的聲音,重新開始創作,比如繪畫,要回到人類最開始作畫的沖動去。中國新詩發展百年至今,經過一百年與國外詩歌的匯合,已經越來越讓人覺得要回到中國本土的審美傳統中去吸取營養,如同不少當代藝術家一樣,都在想方設法回到人類、民族、地方、生命等的過去,重新出發。杜尚的小便池,作為觀念藝術的一個載體,他說的是萬物當你賦予其一個新的觀念,就成為了藝術品,說藝術品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太多了。他說的,也是人類已經賦予了事物太多的觀念,而藝術祛除那些鐐銬。所以,當我們回到故鄉,發現故鄉總是新意盎然。黃永玉說,本事在外面用完后,就要回到故鄉再揀一點。我看,每個文藝作品其中都有本土性的存在,包括現在流行的網絡小說。這叫跑得和尚跑不了廟。

楊厚均以“作為自在的本土性和作為自覺的本土性”為題發言,他認為中國新文學包括中國新詩走過了一百年的歷史。在這個時間的節點上來探討新詩的發展是非常有意思的。中國新詩在主觀是以向西方現代詩歌學習為起點的。但新詩的本土化問題也伴隨著中國新詩發展的全過程。無論是新月派的中西藝術結婚后產生的寧馨兒的表述、還是毛澤東的古典加民歌、還是八十年代后期湖南詩人提倡的新鄉土詩歌都在詩歌的本土化上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在很多人那里,中國新詩似乎存在著西方化與本土化的兩條路徑。我個人認為這是不成立的。西方化與本土化其實只是為了我們表述的方便而出現的一種說法。它們一開始就是一體的。就本土化而言,只要是用漢語寫作,本土化就不是一個問題。作為一種自在狀態,本土、傳統從來就不會消失,并深深地楔入我們生活的所有層面,尤其是語言層面。一個存在了幾千年的傳統,不可能如此輕易地束手就擒。如果我們真的用我們的語言把我們今天在經驗層面最真實最深入最個性化的那一面呈現出來,我們就不擔心有沒有本土化的問題。我們今天討論本土性,更多的意義在于一種姿態,一種對于本土性的自覺,一種愿景。如果我們沒有這種姿態、自覺和愿景,當我們自然而然地把作為自在狀態的本土性呈現出來的時候,我們可能意識不到它的存在,它可能會稍縱即逝,本土性的詩歌表達就變會變得如此脆弱。我們其實無法說清本土性到底是什么,但我們有了這個姿態和自覺,當本土性呈現出來的時候,我們就會立刻捕捉到它,并給予關注,由此推動新詩的發展。
李不嫁認為,本土性其實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對于獨立寫作的個人,他觀察的所謂世界大部分即是地方的(不包括內省和知識),也即是本土性。就我個人而言,要寫出有骨頭、有血性的詩歌,必定離不開自己的生活經歷、苦痛和傷痕,從而折射這片土地、與這個民族的命運,我即是一滴雨,落到了這里,帶著這里的溫度和氣息,唯有詩歌讓它閃光。
夢天嵐認為,百年中國新詩的本土性是一個既成的事實,這個事實是由中國百年新詩的海量文本構成的。我不贊成“漢詩西化”或“翻譯體”的說法,這些說法其實包含著對本土性的漠視。中國新詩的本土性在于其母體漢字,每一個漢字在歷盡數千年的演繹中攜帶了太多的信息,這些信息其實一直在中國新詩中得以傳遞和延續,如同基因和血脈。
肖歌說:在同一座高山,隨著海撥高度的變化,生長在不同海撥高度的植被也隨之改變。植物扎根的本土的豐富性,帶來了植物的豐富性。同樣,在不同地域生活著的詩人們,對每一個體的詩人而言,其生活成長的那個村莊,那個小鎮,那條街巷便是本土,其情感的根總是深扎在腳下的那片土地。詩人觸發、引爆詩寫靈感的那些景、物、人,那些經歷、認知、視角,總會打上本土性烙印。本土性為詩人形成自己的詩寫風格、特點提供了可能。正因為“本土”的多樣性,在中國新詩發展的百年歷程中,形成了一個個具有本土性的詩寫群體,造就了一個個獨具風格的詩人。我認為,既使在人囗流動性加快的當下,本土性對詩歌寫作者來說,依然是一個離不開的視點,對詩歌風格的多樣性的形成依然是一個離不開的重要因素。
周春泉認為,討論新詩的本土性的最基本點,就是必須構建本土的詩歌語言。其實很簡單,就是如何將話寫成詩,把詩說成話。同時這又很不簡單,個中滲透著一個詩人對本土文化的認知傳承和詮釋。從本土語言的演化中,就會體現出一個詩人的本土情懷、生活修養和文化修為。其次在同一本土語境中,必須充分彰顯詩人自已的標識。我認為同一語境,多個詩人多首作品,在語氣敘述方式乃至語言風格同出一轍,這是時下倡導詩歌本土性必須引以重視的問題。詩人的語言是個性的,必須獨立特行。

吳茂盛認為,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們對詩歌“本土性”的強調,就是對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自尊和弘揚。譬如我們湖南詩人在創作中,無不與生俱來般以湖南人的特質,獨有的視覺呈現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和“心憂天下、敢為人先”的精神實質。
幽林石子認為,詩歌本土性的血脈中始終流淌著一股藥性。我相信用靈魂寫作的詩人一定深有體會。每一個漢字、每一個意象就是不同藥味不同作用的藥。
湘陰文藝界代表汪鵬、梁軍、李娃、陳文革、姚娜、郭丹、洪宗甫、李雄飛等也參與了討論,最后詩人們與朗誦家郭永莉朗誦了數十首詩歌作品。湖南省作協副主席、岳陽市作協主席、岳陽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彭東明講話,湘陰縣政協副主席、縣文聯主席熊國庭致歡迎辭。
栗山詩會,田野調查,元詩啟蒙。鑒于湖南詩人黃明祥先生以刻刀般的手法,寫出了有硬度的作品,以赤子之心,拍攝出詩意電影《栗山:父親的床》。周瑟瑟還宣布了由湖南理工學院文學院、中國詩人田野調查小組、《卡丘》詩刊共同向黃明祥先生授予第二屆栗山詩會“2016年度詩人獎”。在詩會現場向其頒發了獲獎證書與水晶獎杯。
紅網記者湯紅輝全程報道。(梁軍)